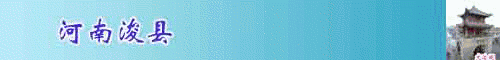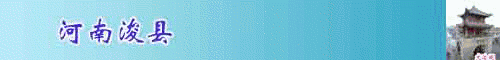|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杨玘屯位于浚县城东,距离大伾山两三里路。站在山脚向东望去,平坦的原野上麦苗青青,村庄如麦田中的孤岛,朴素而安详。
一条小路,将村庄与世界相连。常见的村庄景象,院落外,老人靠墙坐着,安静地享用冬天的阳光;他们的身边,孩子们呼喊着奔跑,不能片刻消停。和一般村庄的村民不同的是,杨玘屯人对我们这些外人的到来并不怎么留意。村子名声在外,村民们已经习惯了各色人等进入他们的生活。后来跟他们聊天,村民说,扛着摄像机的记者,大惊小怪的游人,搞美术的教授、学者,金发碧眼的老外,都是村里的常客,他们早见怪不怪了。
在村子里流连了几天,我们接触了十来位农民艺术家,他们赋予泥巴的鲜活和生动,让我们惊奇赞叹,深深沉醉。从村民口中,我们也了解到了泥咕咕历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历史。不同的时代,泥咕咕对他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有时是一种爱好,有时是一个饭碗,而有的时候,是他们赖以活命的依靠。
在杨玘屯老一辈儿人中,出了不少高人,他们的作品各有特色,风格独具。王廷良以戏曲人物见长,造型古拙厚重;王蓝田注重趣味性,作品形态生动,细腻精致;李永连的作品富于夸张,以豪放著称;侯全德则注重造型变化,作品以新奇著称。但这些前辈高人多已去世,85岁的王蓝田先生硕果仅存。经浚县宣传部新闻科长赵士杰介绍,我们前去拜访了王蓝田先生。
坐在家中摆放泥咕咕的架子前,王蓝田轻声缓语,将我们带进了泥咕咕刚刚走过的这百十年。
小时候的“家庭作业”
跨进王家的大门,王蓝田正带着他的孙子王红杰捏泥咕咕。
老人比较瘦,身穿黑色棉袄棉裤,跟一般的乡下老人没什么两样。虽然满脸都是皱纹,下颌白须稀疏,但眼神中却透着一种生动的气息。家人说,老人85岁了,但每天都要捏些泥咕咕,对于他来说,这是天下最开心、最有趣的事。
见到我们来,老人马上要停下手中的活儿,但我们不愿错过大饱眼福的机会,坚持让他继续捏。只见老人拿起一团泥,捏一会儿用根小棍儿扎扎捅捅,几分钟后,一个小猪捏成,生动有趣,活灵活现,像是一头小活猪要从老人的手中挣脱出来,看得周围的人啧啧称奇。
王红杰随后也捏完了,在我们这些外行看来,他捏得也很好,但总觉得没有爷爷捏得生动有趣。他把自己捏的小猪递过来,让爷爷指点。王蓝田也不多说,只是在小猪身上捏几下给他看。老人说,村里人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学捏泥咕咕,说多了也没用,都是从小在家里看,大了开始捏,捏着捏着就会了。
王蓝田生于1922年,六七岁就开始捏泥咕咕,那时他爷爷像布置家庭作业一样,规定他们小孩子每人每天要捏50个泥咕咕,捏够数才能玩,不够不准出门。
他家22口人,爷爷是掌柜,大小事都管。家里除了妇女,男的都得捏泥咕咕,那会儿讲究男耕女织,女的主要是纺花织布。他父亲弟兄四个,每人面前一块泥,孩子们都跟着各自的父亲干。他父亲捏大泥咕咕,二叔捏马,四叔会捏大头狮子,小孩子们光捏手指头肚儿大的小咕咕。那会儿没多少精美的泥咕咕,生活艰难,做得再好也卖不上价钱,所以不讲究好,只讲究多,多了才能多卖钱。
一家人忙乎一冬,正月庙会去卖,当时庙会很盛,“不管捏多少泥咕咕,都能卖完。”王蓝田说,“每天要往会上担两三趟。”卖完了泥咕咕,爷爷就主持着分钱,小孩儿们也都有份儿,让他们来年干活有劲儿。
从十多岁起,王蓝田逐渐展现出过人的灵气和才华,他捏的泥咕咕灵巧生动,很受欢迎。对于他来说,捏泥咕咕是一件非常有趣好玩的事儿,他不断尝试捏新的东西,看见啥捏啥,喜欢啥捏啥,捏出来就有人喜欢。飞禽走兽,戏剧人物等,都捏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捏神仙最作难,不知道长啥样、啥行头。后来听戏听说书,他就很注意神仙长啥样。吕洞宾是“天子宝剑在他身,柳枝是他跟班人”,这就可以了:捏个老道,背把剑。汉钟离是“身穿八卦衣,芭蕉扇提手里。黄腾腾的风,呼啦啦的雨……”有这几句词,他捏的汉钟离活灵活现。
成年后,除了上浚县的两次庙会,他又开始跟着村里人到处赶庙会,主要是本县的同山会、白庙会、钜桥会等,有时到外省赶庙会。
老人自豪地说,他捏的东西“走哪卖哪”,到处都受欢迎。去山西串亲戚时,他一看那边没有人卖泥咕咕,就弄点土开始捏,没想到轰动当地。“那儿的人跟看把戏一样围着瞧,乱往我手里塞钱,一筐泥咕咕一会儿就卖完了。“
靠泥咕咕活下来
说起往事,老人时常岔开话题感慨。这80年,世界的变化太大了,80年前他童年记忆中的世界,与现在几乎完全两样。
“那会儿都用火镰、火纸媒儿打火,连唱戏用的都是黑油灯。看到个自行车俺们都撵着瞧,稀罕,就俩轮,咋骑着就能走路。”老人热切地说着,仿佛恨不得拉我们回去,看看以前那个世界:“做个梦也想不到,会发展到这个时代!”
老人说,小的时候都很穷,大盐(指海盐)吃不起,用小盐腌红薯秆当菜,“现在的人,吃肉都没味儿!”那时,整个杨玘屯都很穷,村东是沙土地,再往东七八里,都是盐碱地。这一带过去是黄河,虽然已经改道数百年,黄河还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好在地层下多的是黄河淤泥,村里人靠捏泥咕咕,等着起庙会了挣点钱贴补家用,维持生计。所以那个时候,村里大多数人家都捏泥咕咕,不捏泥咕咕的人家,都制作木葫芦、彩蛋等木货(木制玩具)。
老人说,他这一辈子,最难的是在1942、1943年,地里没收成,一家人靠着泥咕咕才活了下来。
“那年先是下雨,一下48天,沟里直往外漫水。然后几个月不下雨,麦子、玉米全旱死了,一亩地收二斗,一斗30斤;第二年除了旱还起了蝗虫,地里小蚂蚱一个接一个往外出,铺了一层,然后飞了起来,遮天蔽日……”
家里没吃的,他母亲只能拿树叶、红薯叶做饭。要活命,只有一条路:挑泥咕咕去外地换粮食。当时王蓝田20来岁,成为全家人的依靠。那时整个豫北都受灾,很多地方饿死人,要走到山西、山东才能换到粮食。
那时正是抗战期间,既有“老日”,又有很多土匪,必须小心谨慎,绕着路走。王蓝田每次出门,尽自己最大气力,“能挑多少挑多少”。走到没受灾的地面,拿泥咕咕换个馍,换把花生,或者换个玉米棒,只要是能吃的,什么都换。
等一担子泥咕咕换得差不多了,王蓝田就往回返,把换来的花生、玉米、干馍、干窝窝什么的挑回家,全家人就靠这活了下来。
成为“民间工艺大师”
新中国成立后,庙会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泥咕咕也不被提倡,但为了生计,杨玘屯人并没有停手。“文化大革命”时,泥咕咕被当做“四旧”,县里一个头头下令不准再捏泥咕咕,派人来村里,把捏好的泥咕咕全部收走了。
村里的地不好,不捏点泥咕咕,很多人家吃不饱肚子,所以大家背地里还捏,捏好了用架子车拉到外地去卖。常有人拦着刁难,但村民并不担心,泥咕咕就是他们最好的通行证。堆下笑脸,他们挑些精巧的泥咕咕送过去,让拦路的人捎回去给孩子玩。看着好玩的泥咕咕,那些人绷紧的脸大多露出笑容,就挥挥手让他们过去。
上个世纪80年代,上边开始重视民间的东西,泥咕咕时来运转,逐渐兴盛起来。
1984年,河南省工艺美术总公司派人到杨玘屯,让村支书帮着收集老艺人们的作品,要从中选一个人到郑州去。王蓝田送了一件活头狮子,最终被选中,由乡里派人,将他一路送到郑州。
王蓝田一出手,省工艺美术总公司的人就瞪直了眼,每捏成一件,都是一阵叫好声。人家看重,王蓝田心中快意,拿出了平生的绝技,连着捏了四天,看得大家无比敬服。后来跟大家熟悉了,坐在一起说闲话,王蓝田说:“能去北京瞧瞧,这辈子就值了。”本来是无心的话,但正好公司也有意送他到北京去表演,很快就派人与他一起去了北京。
四五天之内,王蓝田从村里到郑州,又从郑州到北京,过去养家糊口的营生成了艺术,他也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了众人注目的民间艺术家。在北京,他同样赢得了一阵阵的叫好声,在中央美术馆、中央美院,那些著名的画家、美术系的教授,同样认为王蓝田的泥咕咕是不凡的艺术品。这些专业人士给予他高度的评价,一位画家曾赞佩地说:“其创作题材广泛,作品形象生动,夸张简洁,神采毕现,堪与大写意的中国画相媲美,无论是人物还是飞禽走兽,千姿百态,在粗犷中凸显一种灵气。”
而浚县泥咕咕豪放大气、富有亲和力的独特风格,也受到业界的重视,被专家们称为“中国古文化的活化石”。
1988年,河南民间美术协会正式命名王蓝田为“民间艺术家”,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命名他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
古道热肠甘享清贫
我们聊天的时候,王家来了一拨郑州人,买了几件泥咕咕后,几个漂亮女孩似乎意犹未尽,凑过来跟王蓝田说话。
老人对此早已习惯,他名声在外,常有人来家里买泥咕咕。我们觉得有点奇怪的是,老人成名已20多年,但王家仍很简朴,跟一般农家没什么区别。王红杰告诉我们,他家收入并不高,跟外出打工的人挣得差不多。
浚县民风淳厚,王蓝田更是为人厚道。“来买泥咕咕的,没人跟我还价,都是要多少给多少,很多专家甚至恨不得多给些钱,但我觉得这东西没本钱,地下土做的,要个工夫钱就可以了,要多了跟‘悫人’一样。”老人这样说。
他家的泥咕咕是折合成工作时间定价的,一天能做的30元,两天能做的60元。泥咕咕工艺过程很复杂,取土、和泥、捏制、烘干、窑烧、上色等,他们只能根据经验,将工时大致折合在每件泥咕咕上。
前段时间,省群艺馆的专家倪宝诚打来电话,说他有个日本朋友要去买泥咕咕,一再交代王蓝田:“你要贵点啊,小的要30元!”日本人来了,非常喜欢他的东西,但王蓝田要不出那个价格,他觉得那太贵。后来日本人挑了几十个小泥咕咕,也没问价,按每个30元付了款。原来倪宝诚料到他不会要那样的价格,干脆自己帮他讲好了价格。
很多人被老人的作品打动,更为他的厚道感动,在北京教书的德国人石奥兰(音)跟老人就是好朋友。
石奥兰第一次来王家,挑了190元的东西,可他给了260元。王蓝田说:“你给多了。”石奥兰说:“是你要得太便宜”。
第二次,石奥兰又要了300元的泥咕咕,说他要回德国了,想带回去看有没有人喜欢。过了一段时间,石奥兰又送来了2000元钱,说他把那些泥咕咕放在一个书店的橱窗里,很快都卖完了,这是赚的钱。王蓝田说:“这钱不能收,你给过300元了。”石奥兰说:“这是你作品的价值,我也没拿运费,一个挎包就背回去了。”“非典”前,石奥兰打电话让捏一批小的泥咕咕他带回去,结果“非典”爆发,他没来成。2006年春节,他本来说再来,后来因身体原因没来成。
老人对石奥兰印象很好,他们都是那种天性纯朴的人,交往没有任何隔阂。石奥兰在北京待了10多年,娶了个山东媳妇。他说的话都能懂,但“瞅着不像咱国人”,老人就问他:“你是哪的人?”他媳妇就反问:“你看他不一样?”“是啊,头发蓝。”他媳妇就笑:“他鼻子还高呢。”到现在,每逢过年过节,石奥兰一家都打电话问候。
说起这些,王蓝田心情很好,他觉得泥咕咕给他带来的,已经很多很多。“该我吃这碗饭,85岁了,眼不花,手不颤。”2007年春节前,老人又买了一套《水浒》画册,捏了两套水浒人物,这是他以前从没捏过的。
在杨玘屯老一辈儿人中,出了不少高人,他们的作品各有特色,风格独具,其中85岁的王蓝田先生上个世纪90年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