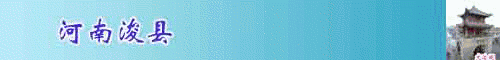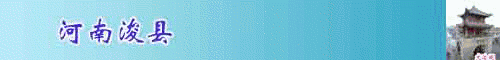|
2008-04-14
16:41:36
曾多次拜谒子贡墓,但都是陪客人来的,早想独自来一次,不带任务,不要干拢。今天终于来了。这是清明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日。
出了东张庄村街北口,就看到了高大的子贡墓。金黄色的坟冢,卧在绿油油的麦田里,犹如屹立在海洋中的一座小岛,几通卧碑和立碑,则像绿色波浪中张开的一叶叶船上的帆。
子贡,这位先贤,不仅生前经历传奇、地位显赫,而且死后也被几代帝王先后追谥为黎侯、黎阳公、黎公,但他的墓地为何这般冷落?为何处在农田里,连块墓园都没有呢?为何他的墓地曾被误祭假冢长达200多年呢?曾有不少拜谒子贡墓的人这样问我。其实,这也是我早先困惑的问题。
壮观墓园 已成记忆
子贡第79代孙端木现堂,今年60岁了,提起以前的子贡墓,他十分痛惜地说:小时候,母亲带我到先人的墓地,感到好大啊,一眼远不到边的柏村林,柏树棵棵都一搂多粗,最细的柏树,都比现在曲阜孔林里最粗的柏树粗好多。不少柏树上,挂着一盘盘蚂蜂窝,蚂蜂窝盘有脸盆口那么大,恐怕蚂蜂窝有一百多个吧。一进柏树林,蚂蜂嗡嗡嘤嘤,很神秘,很肃穆。
东张庄村的老人们回忆说,五十年前,子贡墓挺气派,前边立着石牌坊,进了牌坊门,是甬道,甬道两旁和柏林里,立着各种石兽、石人,5间大殿,殿中立子贡石像,大展西边各有3间廊房。
村民的回忆在地方史志诸多资料里得到了证实,端木现堂曾给我拿出了《端木氏家谱》,“端木子林墓”篇中记:万历庚寅,宁公又于墓前重建孪岗,列东西序修翁仲、石羊、石虎、重门、石坊,额曰“先贤子贡之墓”。明代,礼制规定,一、二品官员墓前才能立石人,石虎、石羊、石马和望柱的。子贡墓之所以享有这么高的礼仪标准,这是因为子贡是孔子最重要的弟子,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就是说,孔子及其学说,能够名扬天下,国因为子贡出了大力,做了别人做不到的工作,所以,后人评价说子贡有“亚圣之德”(《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后汉书·明帝记》载: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东巡,“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从此以后,子贡不断受到历代帝王及官府的祭祀。与此同时,对子贡也不断追加谥号,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为“黎阳公”,政和五年(111年),都水使孟昌龄至浚州,奏准建黎公墓专祠。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封“黎公”。清康熙四十年(1703年),玄烨皇帝西巡返京经浚县宜沟镇,遣太子谒子贡墓。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封先贤,为12哲之一。
子贡既然享誉历代官府的祭祀,他的墓园又怎能不显赫威仪呢?然而,那些石仪、石坊和殿廊,至今都荡然天存了,只剩下了一座坟冢和几通碑碣。
谁人作孽 砸碑平墓
下了土路,我向墓地那通最高的石碑走去。麦苗上的露水,立时打湿了我的裤角和鞋祙,丝丝的凉。这是《改正先贤子贡墓祠记》碑,上面详细记载了子贡墓遭人破坏,移像造假,致使误祭达200多年的史实。
元代之前,来浚县的达官显贵,常到子贡墓谒拜祭祀,香火很盛。元末,东张庄一杜姓村民,恨官府来祭祀子贡拢乱了生活,乘红巾军入浚之乱,夜间平子贡墓,砸碎石碑,并将子贡石像移到了大伾山脚下的一处墓冢处,自元末到明末,子贡伪墓竟被误祭200余年。
一代先贤的墓冢,竟然被误祭这么长时间,听起来不可思议,其实,回忆一下那段历史,就不感到奇怪了。《浚县志》载: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红巾军攻破浚州府衙,火烧清白堂,焚大伾山大佛阁。这时候,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到了明洪武三年(1370年),“浚州人口不满五千,降浚州为浚县。以至从洪武八年(1375年)到永乐三年,先后四次向浚县迁民,张庄村民或许是担扰以后官府祭祀引来不测,就乘乱毁了子贡墓。
滑县与浚县是紧临,子贡后裔,81代孙端木繁正任滑县史志办主任,他说:元末明初那段历史太沉重了,滑县曾是诸侯,帝王建邦立业之地,人口密度大,可是到了元末明初,由于兵连祸接,加之黄水为患,蝗虫成灾,苛捐杂税,生民不堪其苦,举家迁徙,流离失所者不可胜数,滑、浚两县“土著人家,十不存一(明嘉靖《彰德府志》)”。
天灾人祸屠戳着生灵,也亵渎了一代先贤。同一时期,子贡的恩师孔子也遭到了类似的厄运。建于浚县浮丘山的孔庙(又称先师庙、文庙)“元末红巾军起义时,毁于兵燹。”(《浚县志·文物·孔庙》);《曲阜市志·大事记》载:“1357年(至正17年)红巾军毛贵部占领曲阜,衍圣会及地方官坤逃往外地。孔庙祀典废驰数年,庙貌荒芜。”
随着政局的稳定,民众的安居乐业,官府重拾对子贡的祭祀活动,先后在明正统和正德年间对大伾山南的子贡假墓地进行过两次修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县令宁时镆在阅读旧县志时,发现黎公墓在大伾山东南3里许的东张庄村的记载,遂对大伾山南的子贡墓产生了疑惑,就到张庄察访,在一名叫孟博的80多岁的老人指点下,在张庄村北找到了墓穴和子贡墓碑碎石,找到子贡墓后,宁县令随又命人开挖大伾山下的所谓子贡墓,见墓穴洞门石头上题着“萧平川林丘”五字。经查考方知是北宋萧平川与契丹族世婚的贵族之墓,宁时镇报请郡台,将子贡石像移回了张庄,在原址重建墓祠,“抡人为植,筑崇墉,树嘉木,”并立《改正先贤子贡墓祠记》碑。
清代,子贡墓经过多次修葺和扩建后,墓地有了相当规模。墓祠坐北朝南,南端有四柱三间式石坊、过石坊门、南北甬道直达大殿、石马、石羊、文武翁仲排列左右,正殿三楹,供子贡雕像,两翼为东西簃室,大门两侧各建小室,为看守者居住,祠院四周,筑有高墙。正殿之后,是子贡墓,高达3米余有余,整个墓园占地30余亩,建筑“栋宇丽整像设俨备”,古柏参天,百株有余。
屡遭劫难 复成荒冢
子贡墓基本恢复本来的面貌后,一度祭典兴盛,
子贡的诞辰日是农历二月二十七,自明万历二十年开始,每年在子贡诞辰日的前一天即二月二十六,在子贡墓前举行庙会,周围民众“持酒登堂祭子贡”,表达对子贡这位先贤圣哲的敬仰之情。
历史的脚步走进了世纪五十年代,一场劫难也渐渐向子贡墓逼近。1958年,当地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为跨上千里马,跃上新台阶,浚县飞快上马了一批工业企业。一个公社的机械厂研制出了滚珠机,《人民日报》对此作了专题报导,天马电影制片厂又紧锣密鼓地拍摄了《能工巧匠》专题片。这一下更刺激了当地大跃进的积极性,又盲目上马了一大批国营,集体企业。县造船厂为了赶造300吨“国庆号”大船,于国庆节前献礼,在大材料缺乏的情况下,决策者下令砍伐了子贡墓和大伾山景区50余株粗大的古柏。工业在“跃进”,农业系统不甘落后,上级规划开挖大公河,引黄河水灌溉封丘、滑县、浚县、长垣、南乐等县土地。大公河在子贡墓地南北穿过,结果墓地被毁,古柏被进一步被砍伐。由于水利工程缺乏科学性、可行性,不久即报废,“国庆号”大船也因水浅而停航。
在讲到子贡墓遭受的这次劫难时,当地一位姓张的老人告诉我:大伾山上有棵泪柏,浑身上下长着数不清的眼睛,它有好几百岁的年龄了,每逢大的劫难,它的无数个眼睛里都会溢出泪水。子贡墓柏被砍伐了那些天,泪柏流泪了,流得它脚前的泪臼都盛不下了。
老人的说法让我无法得到证实,但老人在讲这段话时,他的眼里却蒙了泪水。
子贡墓另一劫难接踵而来。1974年,刮起了“批林批孔”风,从上到下,层层掀“孔老二”。子贡是孔子高徒,是孔子思想及其学说的最有力的捍卫者,支持者,传播者《论语》、《孔子家语》、《史记》等典籍记载得清清楚楚,名副其实的“孔老二代言人”,原来被敬祭的先贤,一下子成了封建统治,反动学说的卫道士河南省革委会在子贡墓前召开了“批林批孔现场会”。子贡墓受到了洗劫般的破坏,石人、石坊被推倒了,打碎了,小碎石被埋到了地下,大点儿的被村民弄到家,垒了猪圈、盖了鸡舍、修了水渠,那通《改正先贤子贡墓祠记》碑幸存下来了,幸存的,还有子贡高大的坟冢和坟冢上岁岁枯荣的芳草。
儒商精神 生生不息
2007年春秋,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2007年豫港贸易洽谈会”上作了“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主题讲话,其中讲了商业文化,讲了儒商始祖子贡对当代的影响及意义。
不久,河南电视台来浚拍摄子贡的专题片,他们来浚县寻觅的,不仅是儒商始祖子贡的历史足迹,更重要的是探究儒商文化与当今中原崛起的内在契舍点,子贡的经商之道,外交谋略,尊师敬长的精神,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可多得的珍贵文化遗产,先别是子贡的儒商文化,更是可深入开掘的一脉文化富矿,子贡作为儒商始祖,奠定了中华儒商文化的基础,他的经商理念,有着精深的文化内涵,他“不受命”敢为人先,掌握了商道规律,达到了“凢则屡中”的境地;他以诚信为本,在《论语》中,多处记载着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使他在商场中蠃得了很好的信誉,使其立于不败之地;他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做到推己及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互相尊重,互惠互利,他“富而无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慷概回报社会,达到经商的最高境界。“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让陶朱富,贷殖当推子贡贤”,“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这一幅幅世代流传到今仍被商家推崇选用的名联,足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子贡的儒商文化思相影响深远。
河南电视台编导孙宁先生到浚县后,人为子贡故里珍藏的丰富的文史资料感到惊喜的同时,也为能拍摄的文物遗存的不足感到遗憾。当地听了东张村几位村民对当年子贡墓壮观情景的叙说后,脸上显示出了十分痛惜的表情,一位到过“子路坟”、“颜回庙”的村民说:子贡墓比这会儿的子路坟,颜子庙还要气派。要是保存下来,张庄村就不是现在的张庄村了。言外之意,子贡墓若完好会成为一处名胜,会带动这里的旅游经济,村民自然会富起来。
孙宁先生点头。儒商始祖故里在浚县,儒商文化之根扎在浚县,儒商文化之流源于浚县,浚县为之骄傲,但文化是没疆界的,近些年,不仅高层已开始重视儒商文化研究,而且不少地方盯上了儒商文化的开发价值,孔子故里曲阜学院设了“儒商学院”,武汉市已成立了“子贡书院”,这些现象使我不由联想到日本作家井上靖十多年前在小说《孔子》中的话:“目前,在孔门的高弟中,对子贡的研究最为落后,我想不久的将来他可能居于孔门研究中心。”当前的情势,或许正在一步一步验证着井上靖的预言吧。
有惊喜,也有忧虑。十多天前的一个下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人本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阎雨和北京大学教授翟志高先生到浚县来,他们也是为子贡来的。谈话中,阎先生感叹:在北大,那么多国学教授中没有一个讲子贡的;开那么多国学班,也没有一个儒商班,不仅北大,几乎全国高校的工商管理学院,讲的基本是两方的工商管理理论,适合东方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论体系,还没人建立起来。我当时从阎先生的语气里听到了焦虑,我从他的脸面上看到了忧郁。与其告别时,太阳已经西坠,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和翟先生竟在薄暮时蹚访了子贡墓,这是我几天后在他回京后才知道的,我隐隐产生了几丝愧意,可愧意随之被欣慰淹没了:中华儒商文化的理论体系,或许不久便可建立起来。
子贡墓前,我陷入了沉思:公元前520年,您从这块土地上走了出去,隔了几十年之后,您又回到了这块土地,在这里安息了,但您留下精神财富,远远跨过了地域界限,那是属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啊!
我打着火机,在这位先贤墓前点燃了我研究他的几篇和撰写的《子贡传》,心里默念着《子贡传》开头的那句话:“子贡,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他走到了历史长廊的极深处,那是一个我们的目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可此时此刻,透过跳动的火苗和缭绕的青烟,我似乎看到了子贡举步跋涉的背影,甚至清晰地听到了他有力的历史足音。
来源:马金章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