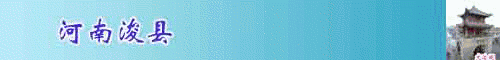|
自大禹导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黄河开始在浚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翻浪扬波,到金明昌五年(1194年)在阳武决口南徙,它共流经这里3200多年。在这漫长而悠远的历史岁月里,黄河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但也因其流徙不定而使很多曾经灿烂的文化湮灭消亡。处于古黄河右岸的白马文化,就是一个因黄河流徙而兴衰的文化典型。历史上黄河右岸的白马山以及因山而名的白马城、白马坡、白马津这一区域因黄河的影响,而出现城池兴衰更替、战事频繁不断、民众信仰变换的特殊的津渡文化,我们暂且把它称作白马文化。
要追寻白马文化,我们首先要弄清白马山、白马坡、白马津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寻遍浚县和滑县境域,现在却找不到白马山的踪迹。它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找到它的确切位置。唐《元和志》、宋《寰宇记》均载:“白马山在滑州东北三十四里。”《开山图》云:“山下常有白马,群行山上,悲鸣则河决,驰走则山崩。”《清一统志》、《重修滑县志》云:“县东北酸枣庙村(酸枣庙村原属滑县,1949年10月划归浚县,今属善堂镇)南有土山,俗名白马山,山上有关帝庙,白马县、白马津、白马坡皆以山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白马山因黄河屡屡决口(据《滑县志》载自汉至宋黄河在白马津一带较大的决口就有六次)或因其他原因颓圮,踪迹湮没,但故址仍存,在今善堂镇马村小学南边仍有10多米高的土堆,上有1997年重建的关帝庙。《滑县志》载“白马坡在县东北10公里,古黄河大堤下。”其位置就在浚县酸枣庙村东、朱村南,一直延伸到滑县的白道口镇和枣村乡,这里的人们仍称之为白马坡。《方舆纪要》云:“白马津在滑县西北十里。”《浚县志》云:“黎阳县(故址在大伾山东北)东一里许即黎阳津,南岸为白马津。”据此可知白马津的位置在今天浚县善堂镇的马村和滑县交界处。
古黄河与白马城的兴废变迁
春秋时这一带已有城池,《水经注》云:“白马济之东南,有白马城,卫文公东徙渡河,都之,故济取名焉”。清《滑县志》载:“今县西北十里余有白马古城。”《重修滑县志》:“白马,春秋卫国漕邑,秦朝时于此始置白马县,两汉因之,晋白马县属衮州濮阳国,后魏置衮州于滑台,白马亦随州徙治,隶司州郭,故城遂废”。北朝及隋唐以后的白马城已不再指此处,现在滑县隋唐以后的白马城遗址也有多处。后赵时,石勒十八骑之一的逯明驻守在白马津,他在白马故城附近筑新城,即逯明垒。《河南通志》云:“黎阳津东岸有故城,险带长河,周二十里,戴延之谓为逯明垒。”《浚县志》载:“逯明垒址在城东7公里酸枣庙与马村之间”。《元和志》云:“逯明故城内有逯明台,在滑州北三十里,即白马津,在天桥津(即黎阳津)东岸。”《水经注》曰:“逯明津又称白马津”。《滑县志》云:“五代时有六明镇(即逯明镇)”。众多史料证明:逯明垒就是北朝以前白马城的延续,也是古白马城津渡城池文化的发展。由于这里紧濒黄河,深受水患和战乱之害,古白马城屡建屡徙,逯明城也屡废屡建。自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南徙,这里虽还有辽阔无际的白马坡,但缺少了黄河天险,加之黄河故道遗留水泽和沙滩造成的交通不便,此地在战略上不再重要,这一历史重镇最终被历史废弃、湮没。清乾隆丁丑《滑县志》云:“逯明垒遗址尚存”。
古黄河与白马的战略地位
白马城临白马津控黄河,北与黎阳津隔河相望,居河南北之要塞,世为兵家必争之地和行旅客商往来的重要南北通道。自古白马之险甲于天下,楚汉之胜负由此而分,袁曹之成败由此而决。《战国策》载:“张仪说赵王曰:‘守白马之津’”;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于大泽乡,继而挥师北上,不战而下陈州。遣部将武臣、张耳、陈余等,领精兵3000人,于七月从白马津渡河,北取赵地。汉高祖三年(前204年)八月,汉王刘邦使将军刘贾、卢绾领兵两万,骑兵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断绝楚军粮道。之后,镇守白马津。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绍进军黎阳,企图渡黄河白马津渡口,寻求曹军主力决战。他首先派颜良进攻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夺取黄河南岸要点,以保障主力渡河。四月,曹操为了争取主动,求得初战的胜利,亲自率领轻骑北上,派张辽、关羽为先锋,急趋白马坡。曹军距白马坡十余里路时,颜良才发现,赶忙分兵迎战。关羽迅速逼进颜良军,乘其措手不及,斩了颜良(据《浚县志》载:颜良墓在县城东7公里酸枣庙村东南1公里处。1973年,村人取土将墓夷平。1976年马村群众将墓掘开),袁军溃败,遂解白马之围。曹军沿河而西,袁绍渡河追之,关羽复击斩袁绍将文丑,顺利地退回官渡。白马坡之战为曹军在官渡之战获胜打下良好基础。隋末瓦岗军曾自此渡河攻占黎阳仓;北宋末年金兵自黎阳南来,经此直下汴梁。白马在历史上的特殊战略地位,让这个繁忙的古渡口同时也是个杀声不断的古战场。滔滔黄河水早已远离了,而古老的白马津仍默默地诉说着黄河的沧桑巨变。
历史名人与白马
白马津为古黄河的重要渡口,历代的达官显贵、文人骚客自此往来于大河南北时,留下了无数的千古名篇。魏黄初四年,曹植在处境险恶、心情悲痛的情况下被迫与弟曹彪分别,悲愤而作《赠白马王彪》;魏王粲在
“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
行军途中作《从军诗》;南朝张正见徘徊在黄河岸边,望
“金堤分锦缆,白马渡莲舟”
而《公无渡河》诗成;唐王维在《至滑洲隔河望黎阳怀丁三寓》诗里发出了“故人不可见,河水复悠然”的慨叹;唐高适的《夜别韦司士》展现了这里“黄河曲里沙为岸,白马津边柳向城”特有的景象;唐刘禹锡在《和滑洲李尚书上巳忆江南禊事》中描绘了“白马津头春日迟,河洲归雁拂旌旗。柳营唯有军中戏,不似江南三月时”的景色;唐李嘉佑在此而作的《赠卫南长官赴任》成为他众多赠别诗中的名篇。另有唐岑参的《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宋欧阳修的《初见黄河》,清王鼐的《白马灵津》等等。最著名的还是诗仙李白的《白马津》。公元752年,唐代大诗人李白跨马背弓带箭来到白马津,准备北渡黄河,游历幽燕。李白站在渡口,大风骤起,频频吹起他的衣袖,坐骑昂首向北嘶鸣。李白顿然生情,便挥笔写下了乐府诗《白马津》:“将军发白马,旌节渡黄河。箫鼓聒川岳,沧溟涌涛波。武安有振瓦,易水无寒歌。铁骑若雪山,饮流涸滹沱。扬兵猎月窟,转战略朝那。倚剑登燕然,边峰列嗟峨。萧条万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扫清大漠,包虎戢金戈。”这一篇篇优美诗作形成了独特的白马“津渡诗”文化,白马津也因此闻名古今。
白马的寻根文化
白马,犹如山西洪洞大槐树,根植了一种深厚的“移民情结”。岭南“白马现象”与中原“槐树现象”异曲同工,都是历史的回音。秦始皇平六国后,派员定“百越”,谪中原50万人戍守岭南,屯居邕钦廉三州,至北宋皇祐年间及南宋初期,又有大批北民南迁。这些北方移民的后裔,自称“祖先从白马来”。宋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侬智高率兵攻占邕州城,杀知州陈珙等千余人,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封官拜爵。宋王朝派狄青率大军前来征剿侬智高后,留军戍守,驻扎在南郊一带,实行屯田。宋军将士久戍邕城,与当地壮民通婚,在此安家落户,解甲为民。赵宋后亭子、白沙、上尧、老口、坪南(后改为平南)一带的村落,是当地留守将士的后裔建立的;也有的从是山东白马苑(山东,古指太行山东。白马苑指今河南滑县,包括浚县善堂镇南部)迁来的,至今已有76代。宋熙宁年间,交趾李朝派兵攻占邕州,宋王朝任命陆逵、赵禼为正、副招讨使,率领10万大军南征,击溃交趾侵略军,收复邕州后,又留下一批军队戍守,以加强邕州的防务,其中有一部分将士落籍南宁。岭南的谭、黄、龙等姓后裔都以白马为寻根地。解放前后,有不少岭南人先后到河南找白马寻根。
白马与民间信仰
滔滔古黄河,在孕育白马文明的同时也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许多灾难。这里连绵不断的战火使人民经受家破人亡之痛,黄河频繁的决口使百姓饱受流离失所之苦。为了生活的安定和生命的安全,南北朝时这里的人们就在白马城外,黄河大堤上(寺址在今善堂镇酸枣庙村和李村之间,上世纪70年代拆除)建了一座寺院――佛时寺,希望用佛来镇住黄河,这和后赵石勒在大伾山东崖雕凿大石佛以镇黄河用意相同。从现存的佛时寺北齐武平三年的四面造像碑(1964年秋,文化部借调此碑拟到日本东京展出,因故未就,现藏省博物馆)及历代残碑的载述可以看出当年这里佛教的兴盛。随着黄河的南徙,水患远离了这里,用佛力镇黄河已失去实际意义。宋代以后历代帝王对关羽的崇封,这里的人们找到了一个新的信仰对象――关帝。在这关羽建功扬名之地,人们对关羽的信仰慢慢超越了对佛教的信仰,关帝庙逐渐取代了佛时寺的尊崇地位。据记载,明清时期浚滑两县不论县城还是乡村几乎到处都建关帝庙,尤其是白马坡一带,村村有帝庙,家家敬关公。明嘉靖四十年,浚滑人士近庙而居者,捐资在原关帝庙址上(在今善堂镇马村)重修庙祠三间,建碑亭一个,并于亭中立白马坡刺颜良图碑。此处的关帝庙因其处在关羽刺颜良之白马坡古战场上而香火更盛,也更显尊崇,更有灵气,“帝庙著灵”被列为滑县十二景之一。清代张同堂来此瞻拜之后,留下了“匹马冲开百万兵,袁军丧胆魏军惊。苍松古柏威灵在,风雨犹闻赴敌声”的诗句来赞美这一美景。直到民国时期,这里仍“庙宇巍然,威灵尚在,远而望之,苍松古柏森列于崇冈之上,风声怒涛,犹凛然有生气”(《重修滑县志》)。关帝信仰是人们对白马英雄的怀想,同时也是白马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这里还因庙而兴起了庙会(农历正月十六),直到解放前庙会还很盛大(庙会涵盖今浚县和滑县的马村、酸枣庙、朱村、宋林、鱼池、白庄等18个村庄),不但远近的民众来敬香朝拜,周边村庄的社火还进庙表演朝拜。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庙宇被盘踞在这里的滑县顽杂兵匪付之一炬。
白马山、白马城、白马津都已成为历史,但白马文化仍在延续和传承。古老的白马津仍能令人遥想当年商船连樯、千帆竞发的繁忙景象,一望无际的白马坡仍在述说着历史的沧桑变迁,白马寻根已成为一种情结,将白马和“白马人”紧紧的连在一起。
朱光临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