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本文作者认为:水清、水量足、竹多是淇河三个最显著的原生态特点,揭示并使更多的人认识这些特点非常重要。作者认为,今天,我们尽管不可能完全恢复淇河历史上的原生态,但是我们了解了它历史上的原生态特点,起码可使我们明白恢复原生态工作的方向,这对进一步认识淇河深厚的文化内涵,适度开发利用淇河的旅游资源,建设文化鹤壁,发展鹤壁市的旅游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今天,所有到过淇河的人,无不为它那鱼翔浅底,沙石可数;杨柳倩姿,倒映水中;积水深处,碧玉晶莹;水坝飞瀑,白雪千堆——水质罕见的清纯而惊异不已。
也无不为它那林木夹岸,清荣峻茂;滩渚湿地,红花绿草;蒹葭翠竹,成丛连片;鹤鹭鹳凫,出没嬉戏——无处不景而啧啧称奇。
虽然今天的淇河看来仍然如此优美,但可以肯定,淇河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原本比今天更生态、更迷人!
淇河是一条生态长廊、一座文化宝藏。我们越深入其中,就越感觉它令人心驰神往、心旌摇曳!笔者从古诗文中发现大量涉及淇河不同历史朝代生态状况的文字,本文拟从最具特色的三个方面略谈一下淇河的原生态状况。
淇河水质何纯美
淇河水质的纯和美,曾深深感动过历代的迁客骚人们。在淇河古诗文中,他们几乎用尽了天下最美的词汇来形容赞誉它。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这淇河水质的纯和美应是淇河几千年来在生态方面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也是它骄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朝无名氏的《张公神碑歌》里“綦(通淇)水汤汤扬清波”诗句中的“清”,是最早咏及淇河水质的最朴素最平实的词语。
南朝梁·沈约《春咏》:“碧水复盈淇。”“碧”即“碧玉”,质地细腻如墨绿色凝脂,很少有瑕疵,历来是玉雕工艺品的上乘之选,也曾是历代宫廷中常用的玉种。一个“复”字,可以使我们想见,淇河水的“碧”,绝非偶尔或短时间的现象。
无独有偶,诗仙李白在《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中,也有一以“碧”喻淇水的名句:“淇水流碧玉。”
两朝诗人都用“碧”来喻淇水,可见诗人心目中的淇水是多么圣洁,多么尊贵,多么令人珍惜怜爱。
北宋·邵雍《寄杨轩》:“淇水清且泚。”“清”和“泚”意思相近,作者连用,可见淇水实在是清上加清,比清还清。
南宋·魏了翁《寄题王才臣南山隐居六首:竹亭》:“淇水凝寒绿。”“凝寒绿”,“凝寒”意为严寒。看来,淇水的“绿”是最刺激作者感官的。那“绿”,简直让他感到阵阵发冷,心旌震撼!
元·马德华《淇门飞雪》:“淇水日夜流……停舟叹清绝。”好个“清绝”,清得绝顶,无以复加!
中国元朝思想家教育家、曾隐居苏门(今辉县市西北之苏门山)的怀州(今沁阳市)人许衡《齐鲁集·谢梁安抚》:“太行西对千峰玉,淇水东窥万斛珠。”诗句以苏门山为坐标点,西面是秀美如玉般的太行群峰耸峙,东面是满河晶莹剔透得浑如珠玉的淇水流淌。作者眼中的淇水是何等澄澈清纯,作者对它又是何等欣赏与珍爱有加。“淇水……万斛珠”,与李白“淇水流碧玉”异曲同工。
明·张维藩《山、水、竹、民歌》:“其二歌曰淇之水,湜湜其流清见底。”湜湜,音shíshí,水清澈貌。这岂非今日之漓江!
明·袁中道《淇县道中值雪》:“淇水益澄鲜。”益澄鲜,意为更清新。这是作者雪天里途经淇水时,所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古籍记载,明孝宗弘治年间,“嘉兴邹汝平归东邱,掘古井,得泉甘冽,名‘绿香泉’,乞名人为图及诗文”。明·伍常《题绿香泉古井》在赞誉“绿香泉古井”的水质时,认为绿香泉古井的水质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地脉潜通淇澳水”,显然作者认为“淇澳水”是天下最优质的水,而且在作者眼里,这“淇澳水”简直有点儿无上“神圣”。
淇河水质之佳今天仍誉满天下。长沙有个取名“竹淇”的老字号个性茶楼,茶楼上有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湖南商学院中文系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授、书画家陈书良的对联“竹篁宜听鹂,淇水好烹茶”。据说这家茶馆,朝迎五湖客,夕有四海宾,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据店主说,这与茶馆的名字“竹淇”两字有着一定的关系。“竹”即茶叶的形状,“淇”乃水源之意。从《诗经·淇奥》起,淇园绿竹的“猗猗”美姿,凭借对卫武公的歌颂,已和人的高尚品德、健全的人格、渊博的学识和俊美的外表等联系起来,淇园竹被称为“淇园君子”。古人有“数竿君子竹,一径美人花”(清·丁瀚《春日偶题·临江仙》)的诗句。因此,这里的“竹”不仅寓意店主人,也包括所有的茶客们,都是人品高雅之士。再说“淇”,历来品茶的人无人不晓茶与水的密切关系,若得不到好水,再好的茶也烹不出好味来;那么淇河之水就是这种名满古今、誉贯天下的最宜烹茶的好水。其实,这家茶楼不可能真的千里迢迢到淇河里取水,店主人以“竹淇”名茶楼的深意,要的就是这“淇”的水质尚佳的名声和它们富含的文化韵味。
常言道,水是茶之母,壶是茶之父,茶壶的功能在于泡茶,茶汤的孕育与最终形成,壶的作用不容忽视。紫砂壶被誉为“冠绝一世,独步千秋”的艺术佳品。紫砂壶壶铭更使这一高贵儒雅的艺术品锦上添花。民国时期的著名紫砂艺人汪宝根,宜兴蜀山人。出自汪宝根先生之手的一把自铭“高风亮节”的竹节壶,壶身正壁,作者运刀成字,篆以十六字楷书,为“直节虚中,有德能容;淇泉渝茗,益引清风”。淇泉,是淇水和泉源水两条河的合称,典出《诗经·卫风·竹竿》:“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淇水在右,泉源在左。”渝茗,俗称泡茶、煮茶、烹茶。清风,指高洁的品格。这竹节形状的紫砂壶,再加上赞颂竹子和淇泉的这一壶铭,将“竹”与“淇”这两种几千年来就同在一起、无法分离、文化和精神内涵丰富的事物或词语,巧妙地融合起来,真是珠联璧合、绝顶艺术,耐人涵咏品味。试想,书房的书桌上放着、或手里端着这“高风亮节”竹节形紫砂壶,壶里盛着“淇泉”水所煮之茶,那是一种何等高雅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不由得使人自然联想到,这竹节形紫砂壶的主人一定是具有竹子般“直节虚中,有德能容”的“高风亮节”,或更益于陶冶高洁的品格。这淇河之水再加上淇奥之竹,其中的意蕴也太令人咀嚼欣赏不尽了!
另见一仿鼓壶(鼓形紫砂壶)上的一段壶铭:“看山如看画,听水如听琴,水流碧淇转。”前两句有一副联语与其意思相类:“青山不墨千秋画,碧水无弦万古琴”;“水流碧淇转”,水是碧淇在流动。三句十五个字,有声有色有动有静。仔细品味,这“声”——“万古琴”声即淇水流动之声;这“色”——“千秋画”应是淇旁之山。看来这“碧淇”是当然的“声”、“色”、“琴”、“画”之经典和样板。这三句壶铭虽未将“碧淇”之水与“烹茶”联系起来,但其中“碧淇”之“碧”的重要性和分量仍是无法掩饰的。
淇河水势何汤汤
历史上的淇河不仅水质绝佳,而且流量水势要比今天大得多。淇河是条小河,若论流量水势,不论曾多大,都无法与长江黄河同日而语。但在同类的河流中,文学史上唯淇河曾有的流量水势被记录在这么多的诗赋中,这一点确也是绝无仅有的。这应是淇河又一主要的原生态现象之一。
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有“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句。汉代的《张公神碑歌》中有“綦(淇)水汤汤扬清波”句。“汤汤”之意,水势浩大、水流很急的样子。这反映的是汉代及其之前的淇河。
西晋诗人陆云有“会如升峻,别如顺淇”句。会,会面,相逢;如升峻,像登山。别,分别;如顺淇,如顺淇而下。极言人生难逢易别,内涵珍惜相聚,惧怕或不忍分离之意。可见晋时的淇河不仅水势大,而且水流急。今天我们看淇河,是在有多道拦河坝的情况下,河水才得以较多地留存。虽有些河段地势平缓,水平如镜,波澜不惊;但从整体来说落差明显较大,这就是我们尚可从局部河段看见浪花翻卷、水声震耳的原因。这一点从淇河的别名——“响河”,便可略知一二。可惜西晋时淇河那样的水势也许一去不复返了。
明朝王世贞《思归引(一曰离拘操)》:“淇水浩无津,方舟曷相援。”淇水浩瀚,找不见渡口,相并行的两只船怎能相互援救!当时水大流急的情景让人感到险象环生。
明朝魏大本《淇水》:“隆虑山下水,冲突七盘隅。涧道东南注,滩声日夜呼。蛟龙潜洞壑,鹳鹤老江湖。绿竹千年种,临流想卫都。”明朝陈孟懋、刘希鲁同题诗《纣窝滩声》分别写道:“波涛滚滚如雷吼”、“时时澎湃惊人耳”。明朝海岳子《淇邑胜杰》:“淇水非殊翻雪浪。”这些诗句都写出了当时淇河的流量和水势之大。最典型的是明朝傅国庶的《白龙潭》:“一水奔流万壑惊,悬波直下怒声轰。若非呼吸关神力,那得风雷竟日鸣。”淇水旁原白龙庙下的白龙潭,悬波飞流直下,怒声如雷,竟日轰鸣,万壑震惊。短短四句,描绘出白龙潭淇河的浩大气势,读来涛声犹如在耳,飞瀑如在眼前。诗中描写的景象今天我们也已无从看到。
清朝杨时壮、杨时复描写淇河白龙潭的同题诗《白龙潭》分别写道:“万流穿山至,飞涛溅渚洲。喷云潭似冶,飞露夏成秋。爱听溪中吼,还期天际流。”“粼粼怪石涌珠泉,百道飞来卷曙烟。怒落沧溪成暴吼,倒嵘雪浪不停漩。暮云惊响栖孤屿,朝日穿崖识洞天。自是深宫深万丈,故多雷电绕门前。”两首诗异曲同工,诗中的“万流”、“百道”、“万丈”、“飞涛”、“喷云”、“飞露”、“怒落”、“暴吼”、“倒嵘”、“雪浪”等词语,生动地刻画出了淇河水势排山倒海、凶如猛兽的状态。
淇河的水势和流量,还可以从历代诗词中常常歌咏到的舟船纵横的情况看出。“淇水滺滺,桧辑松舟”,是最早的先秦时代《诗经·竹竿》中的句子。琢磨西晋·陆云的“会如升峻,别如顺淇”诗句,句中虽未明说坐船相“会”,坐船“顺淇”而下相分别,其实肯定是坐着船的。唐朝李白《魏都别苏明府因北游》中写道:“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元朝马德华《淇门飞雪》中写道:“淇水日夜流……停舟叹清绝”;明朝黄哲《秋月篇》中写道:“关山随别骑,淇水送行舟”;清朝魏源《重游百泉四首:其一》中写道:“残雨啸台山,归人淇水渡。”这些诗句说明清朝时淇河的水势和流量仍很可观。至少从《诗经》所反映的时代起到清朝的魏源时代,淇河的水势和流量仍一直是可供百舸争流的。
淇园绿竹何猗猗
从历代大量触及淇河的诗文中留存下来的信息我们可看到,从殷纣王时起,三千多年以来,淇河的生物品种是何其繁多。但在生物品种方面,淇河历史上最骄人、最突出的特点是淇园之猗猗绿竹。从大量的诗文中可以看到“淇竹”无论从历史之悠久、生长之繁盛、品种之多、繁衍之广、功绩之大、名声之显赫诸方面,都绝无出其右者。毫无疑问,这又是淇河最显著的原生态特点之一。
一般史书认为“淇园”是“卫之竹园”,由春秋时卫武公所建。六朝人戴凯之《竹谱》却说:“淇园,卫地,殷纣竹箭园也。见班彪《志》。”明朝袁中道的《袁中道集》中也有这样的话:“予记班彪《志》曰:‘淇园,殷纣之竹箭园’,又不始卫武公矣。”查更早的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上记载:“(纣王)十七年,西伯伐翟。冬,王游于淇。”这里的“王游于淇”虽未明说游的是“淇园”,但完全可能就是淇园。因为三千多年之前的淇河可观赏的景致,除了清澈晶莹的碧波外,还应有个景观较集中的地段或景点,当时的交通条件绝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安步或乘车沿河几十里游览淇河。这“较集中的地段或景点”应当就是淇园。这说明,淇河的竹子历史的悠久,它的高雅和秀美,三千多年前就已经被我们的先人所欣赏和推崇。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竹园。
淇竹历史上曾为社会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据《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记载,黄河在瓠子决口,二十多年堵不住。“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帝既封禅。乃发卒万人,塞瓠子决河。还自临祭,令群臣从官皆负薪。时东郡烧草薪少,乃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卒塞瓠子”。据《后汉书·寇恂传》记载,寇恂为河内太守时,讲兵习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可见当时的淇园之大、竹子之多。
淇园之竹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先被写入文学作品——《诗经》的。开竹文化之先河的《诗经》中曾7次写到“竹”,其中有5次出现在《国风》中的《淇奥》、《竹竿》两首诗中。《淇奥》一诗以淇园之竹比兴,歌颂功德盖世、才貌双全的美男子卫武公。“淇竹”因此而名冠天下,誉满古今。在历代涉及淇河的大量诗文中,“淇园”也因之而成为竹子或竹园的代名词,这种现象在《诗经》之后的历代诗文书画中屡见不鲜。
“邠苇载《颂》,淇竹传《诗》”(清·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卷六十五:《唐故魏州昌乐县令孙君墓志铭》)。这里的《颂》指《豳风·七月》,《豳风·七月》又被称为“豳颂”(豳,音Bīn,同邠,周的故国,即现陕西省彬县)。《豳风·七月》:“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萑(huán)苇,芦苇。因“豳颂”中咏及芦苇,所以芦苇被称为“邠苇”。“邠苇载《颂》”既有邠苇使“豳颂”得以流传之意,又有邠苇因载于“豳颂”而得以名显后世之意。“淇竹传《诗》”,因《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首开诗歌以淇园之竹作比兴之先河。所以,“淇竹传《诗》”,既含淇竹使《诗经》得以流传之意,又含淇竹因传于《诗经》而流芳百世之意。可见,淇竹对《诗》来说何其重要,它和《诗》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关系何其非同小可。
南宋卫宗武《和新篁韵》:“竹君清绝润于玉,谱牒出自淇之澳。”谱牒,原指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此指记述竹子的品种、特性、功能、产地等的《竹谱》,由晋·戴凯之撰,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谱牒出自淇之澳”,可见淇澳之竹在中国竹子的生产中曾有过的地位、名气及作用。另有花鸟画谱之竹谱叫《淇园肖影》。《中国版画史图录》载:中国画兰花图谱叫《九畹遗容》,简称《兰谱》,梅谱叫《罗浮幻质》,翎毛谱叫《春谷嘤翔》,人物画谱叫《天形道貌》,“竹谱”叫《淇园肖影》。清康熙9年(1670年)增修的《河南通志》物产卷中,记载淇县一带竹品种时有这样的话:“今其地有紫茎竹、斑竹、凤尾竹、淡竹数种。”这些资料说明,淇园之竹曾经有产量高、品质好、品种多的特点,曾在中国竹子及竹文化的发展史上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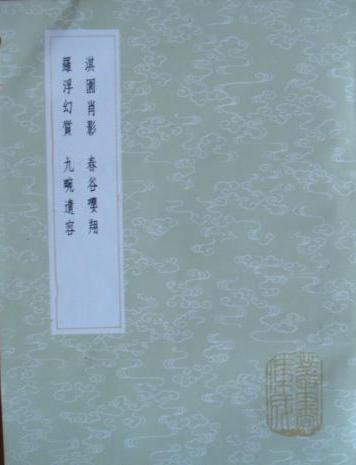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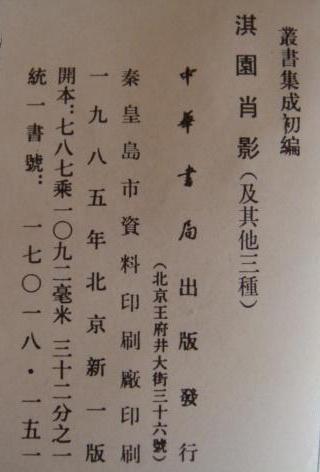
淇竹曾被广泛移植,在全国繁衍,淇园是我国竹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因此古诗文中很多情况下“竹”和“淇竹”是同义语。
南朝诗人沈约《郊居赋》:“其竹则东南独秀,九府擅奇。不迁植于淇水,岂分根于乐池。”沈约的别墅在南京钟山之下。今天的南京东郊,虽然六朝的庐舍庙宇连瓦砾也难得一见,但猗猗绿竹仍然是处处葱茏翠绿,是南京人引以为骄傲的城市山林。沈约认为这“东南独秀,九府擅奇”之绿竹不是“迁植于淇水”就是“分根于乐池”。可见“淇水”“乐池”竹子的名气之显赫、地位之高贵。但这里的“乐池”并非舞台前那一块凹下去的乐队专用场所,而是神话中的池名。《穆天子传》卷二:“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相传,周穆王率兵西征,至风光秀丽无比的黑龙潭,便令在这里演奏广乐三日,爱妃盛姬载歌载舞,后盛姬因妖魔作乱而丧命,周天子葬盛姬在黑龙潭边,并亲手在冢旁和黑龙潭四周种植了盛姬生前喜爱的翠竹,把黑龙潭改名为玄池,也有人叫它“乐池”。“乐池”之竹虽名贵,但那是仙境之竹,可望不可即。现实中真正的名贵之竹只能是淇园之竹而已。
北宋黄庭坚的《次韵文潜同游王舍人园》:“移竹淇园下,买花洛水阳。风烟二十年,花竹可迷藏。”南宋·魏了翁《鹧鸪天·次韵李参政壁朝阳阁建成》:“淇以北,洛之阳。买花移竹且迷藏。”看来中国历史上淇园之竹是竹子的繁殖基地,洛阳是国色天香——花王牡丹的繁殖基地,应确为历史事实,并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咏归堂隐鳞洞之四》:“种竹淇园远致君,生平孤节负辛勤。”“咏归堂隐鳞洞”位于福建南平藏春峡。藏春峡是当时北宋南剑州文化发祥地、儒学活动中心之一。王汝舟等名人曾在藏春峡读书论学。“种竹淇园”的正常语序应为“种淇园竹”,并非到远离福建数千里的淇园去种竹。这里的“淇园竹”,其实指的就是一般的竹子。
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孙子岳珂在《东坝以里沿岸人家皆对门植苇于小屿不晓其旨漫成四绝》一诗中有:“北都旧产无淇竹,见说园池芦苇多”句。东坝以里沿岸人家都在对门的小屿种植芦苇,岳珂对此明为“不晓其旨”,实则反映了作者由所见广种芦苇的现象,引起对“淇竹”的怀念,曲折地表达了对沦陷旧都汴梁和故土的向往。这里的“淇竹”其实也就是一般的竹子,所以将“竹”与“淇”联系起来,可以从中看出“竹”与“淇”天然悠久的渊源关系。
南宋李曾伯《管顺甫以湘竹为青奴儿贶为名湘夫人赋以谢之》:“妾家淇园北封君,厥祖慈事宗苍筼。子孙异代贞节闻,枝分一派从南巡。千古流落湘江滨,几番雨露敷新荣。”所谓“青奴儿”,即夏日取凉寝具,用竹青篾编成,或用整段竹子做成,又名竹夫人。贶,音kuàng,赠,赐。诗中告诉我们湘江滨的湘竹,就是北方曾被誉为“君子”的淇园之竹,曾“枝分一派从南巡”而“千古流落湘江滨”的结果。
明·陆容《满江红·咏竹》:“问华胄,名淇澳。寻苗裔,湘江曲。”问华胄,问竹子是哪个贵族的后代。华胄,帝王显贵的后裔。淇澳,即淇奥,淇河岸的弯曲处,淇园所在地。苗裔,子孙后代。湘江曲,湘江弯曲处。看来直到明朝,人们仍然认可淇园之竹是竹子的祖先,而且这祖先地位显贵荣耀,非同寻常;并确认潇湘之地的竹子,就是淇园之竹的后代。
水清、水量足、竹多是淇河三个最显著的原生态特点。揭示并使更多的人认识这些特点,笔者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尽管不可能完全恢复淇河历史上的原生态,但是我们了解了它历史上的原生态特点,起码可使我们明白恢复原生态工作的方向,这对进一步认识淇河深厚的文化内涵,适度开发利用淇河的旅游资源,建设文化鹤壁,发展鹤壁市的旅游业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摄影 赵永强)